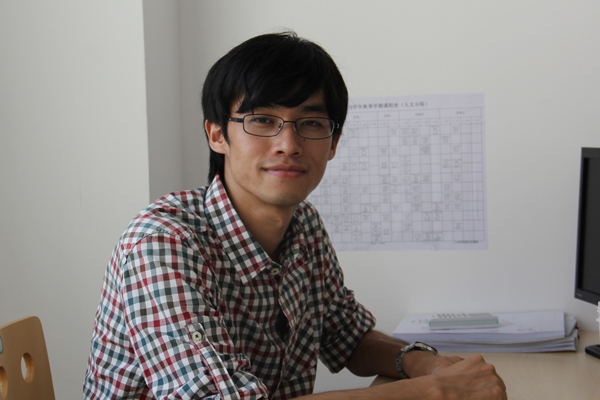
人物简介:刘伟,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副院长,文学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文艺学专业。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会员;先后于《民族文学研究》等核心或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4篇;受邀参加“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等国际国内会议并宣读论文6次;发表其他各类文章40余篇;获得校级至国家级奖项20余次;现主持科研项目2项。主要承担的课程有:民间文学、中外名著导读、文献检索与利用、西方文论等。
记者:谈大学,您有什么看法?
刘伟: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对于大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有共性的,也有个体独特的认识;有身处其中感性的体认,也有将其作为对象相对理性的分析。大学作为一个概念或者知识,我们要把它还原到最初的语境中,作考古学或者谱系学观。现代的大学肯定与西方原来的学园,中国以前的书院、学堂都是不同的,即使在大学产生的西方,大学观都经历了纽曼为代表的古典时代和弗莱克斯纳为代表的传统时代,一直到今天的现代大学。在今天,美国著名的教育学者克尔(clark kerr)把综合化的大学称之为“巨型大学”(multiversity),认为之前古典的、传统的大学都已经失落了,这种表述颇为符合后现代特征。克尔认为今天的大学更像是一座城市,它是由不同社群和文化主体构成的多元中心的机构;是一个具有多重教育目的、多重教育职能、由多个社群构成的新型社会机构。在今天,高校的合并、大学的扩招和大学城的建设都在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上证明了克尔学说,巨型大学已经成为了我们庞大城市的一部分,甚至就是城市本身。同时克尔也总结了现代多元化巨型大学发展中的三个模式,也就是博雅教育的英国模式、研究型的德国模式和社会服务型的美国模式,这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产物,三种模式孰是孰非并不好判断,但在今天这三种类型似乎都是大学题中应有之意,也就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而中国的现代大学本就是晚清五四的舶来品,同样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但时间更为浓缩。1917年蔡元培办北大,秉承的就是欧洲模式,既有英式的博雅教育,也有德式的科学研究。到了1925年清华大学则是沿袭了美国模式,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大增强了。而到了建国后,又统统向内转,开始学习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等于是更加窄化的欧洲模式,有学者指出它造成了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过分强调专业教育,专业壁垒严重、就业选择狭小,这些流弊影响至今,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北大曾提出办学的十六字方针,也就是“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算是对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了。
我们可以在大学的历史中看到,今天的大学肯定是与现代社会契合的产物,但这种契合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影响,如今大学出现了不少问题:大使得尾大不掉,精使得各自为政,尖又造成高处不胜寒。现代性的胜利反而给这个独特的机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高校一直在呼吁改革,从体制到教学、管理各个方面,为的就是让大学更加健康地发展。
记者:从您刚才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经历的变化发展过程,从组织形式、社会功能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那您认为大学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
刘伟:其实任何学校的兴办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教育,虽然学校也承担了科研、服务种种的功能,纽曼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大学的目的是科学与哲学的探索,那么我真不知道大学为什么要招收学生”。可见教对学生的教育是大学最为重要的职能。教育是什么?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是一种培养、模仿与劝善。而且教育的主体和对象必然是一个个的人,虽然“人”这个概念在后福特社会中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自尼采以来的传统,人文科学经历了种种危机,到福柯那里就已经宣称“人死了”,这里的“人”当然不是活生生的肉体,而是我们以往对人的定义在今天统统失效了。虽然面对这样一个变幻不定的主体,但教育仍然是塑造理想人格的事业,只是在今天我们的这种工作要更加谨慎和多元,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定要把人塑造成什么样,同样也没有标准的方法去这么做。
但是多元不代表无序,正直、公平、勤奋等等依旧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刘易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教育首先是塑造人、成全人、培养人,在今天总是觉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给人身上不断添加附加值的过程,“人”的塑造似乎在初等教育中就应该完成。这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关键是各个教育的环节似乎都忘记了“人”的培养,而只注重“技”与“能”,当幼儿园就在学英语、小学就是学奥数的时候,这个任务已经不断推迟和延宕了。而且培养人并不仅仅是道德感的强调,还包括对自身、他人、社会的正确认识,包括沟通与交往的哲学基础和实践要求。所以在高等教育中,“人”仍然是中心和重点,至于“能人”的“能”、“达人”的“达”、“聪明人”的“聪明”只是后来的附加物罢了。
记者:那您认为怎么样去实现培养“人”的目标?
刘伟:对“人”的培养肯定不是靠灌输与讲授,而是要依靠交流与感染,其实知识的传授也是这样,从柏拉图、孔子、阿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学问更是在不断的交流、对话和辩难中产生和传递的,你去看拉斐尔画的“雅典学院”,中心便是柏拉图和阿里士多德的辩论,这也是自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以来西方教育的传统,东方亦是这样,《论语》就是孔子和弟子的对话的产物。但东西方的这种传统在现代大学兴起之后似乎都衰落了。我们今天回过头看,近代中国有个纯粹教育的典型,也是那个大师辈出年代最好的代表,也就是西南联大,它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算是教育的佳话甚至神话。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曾经概括了西南联大师生之间的关系,他称之为“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懦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教师在日常接触中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与情绪裁节”树立楷模。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所以当时闻一多、钱穆、燕卜逊等等学者的宿舍成为了师生交流的第二课堂。这种师生之间、学校同事之间融洽的关系似乎在现代大学强有力的科系分野和科层制度中消失了,怎样在现代体制下适当恢复这种良好的传统,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要发展一种新型的师生、师师之间的关系?
刘伟:不错,其实既是一种发展,也是一种回归,这种对话的关系在前现代,不止是西方的学园,中国的书院也是这样,由一个富有学识和人格魅力的导师将学生统一在一起,交流、互动与对话是基本的形式。书院的兴起是由于官学之弊,两宋期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所以才有民间力量的勃兴,我们学校本来就是民间办学的典型,是不是能从历史中取点经,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像前一段时间,复旦大学、苏州大学等国内高校就开始尝试书院制的管理模式,适度地恢复了通识教育和专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就是不错的尝试。
其实现代大学的兴起,专业化造成的专业壁垒和科层制成为了学园和书院模式的终结者。但就像有学者说的:“一般的校园作为一个社会环境更适合于通才之间的横向接触;而各个分立的学科则更适合于独立学科领域里的专家之间的垂直接触。因此,校园更取向于内部关系,而学科更取向于外部接触”。用学科代替校园的结果就是横向的接触变少了,知识变得更加局限和自给自足,形成了众多的小圈子,学术的小圈子乃至影响到了人际的小圈子、权力的小圈子,久而久之,学校内部的联系度被削弱了,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知识与人际的交往。而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跨学科的交流是必要的,在知识的生产和人际的交往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师生之间、教师之间、教师与行政人员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是非常有益的。
记者:刚才我们宏观地谈了谈您对大学整体的认识,下面您能结合一下专业,谈谈大学中人文科学的情况吗?
刘伟:在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衰落是不争的实事,生源少、就业难,并以此形成恶性循环,加上专业惰性比较强,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都是摆在从业者面前的问题,由此保守的安于现状者有之,敦厚的反思者有之,激进的评判者也有之。造成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的大环境影响到个人选择,个人的考虑又形成大环境的恶化。社会上对专业认识的短视是原因之一,但就像英国绿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所说的:“这些崇尚效率的办学理念执意要边缘化人文与艺术,只告诉我们为了赚钱而存在的商科和为了延年益寿的医科能够让人活到90岁,可如果没了人文艺术,谁有兴趣活到90岁?”但更多人并没有这么清醒的态度,在物质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时候,物质的愉悦和刺激会带来短期的满足,但一旦科技创新速度下降,同质化出现,当iphone5和iphone3区别不大的时候,依靠科技体验和购买带来的快感还能剩下多少。人文科学并不是追求速度感的学科,创新的快慢并不是衡量的标准,所以我觉得人文科学要学会向前看,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面向未来,而且人文科学不是服务社会的,而是引导社会和改变社会,输入良好的价值观、社会观和审美观;同时人文科学也要学会向后看,保持中立性,允许一定的滞后性,用传统去梳理纷繁复杂和尚无定论的种种现象。
记者:如您所言,人文和社会科学可能在大学中承担着更多的精神方面的塑造,像三亚学院普开设的人文通识课正是这方面的努力,最后,想请您由此谈谈大学精神的问题?
刘伟:今天高等教育经常会论及到大学精神,中国自现代大学建立伊始,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诸先生都有所论述,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大学目标、大学文化息息相关,虽然相对务虚,但其重要性毋庸讳言。中国的大学精神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取法于本土古代精义的不在少数,所以很多大学校训都摘自古籍。而且一直以来,关于大学的二分法中,精神要远重要于物质的部分,所以梅贻琦校长的一段话大家耳熟能详,那就是“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见高素质的人才以及人才所创立的氛围才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一所大学的精气神,而神焕则形具,神散则形灭。这些都是现在大家公认办学的圭臬,大学精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这里我也想说精神与气质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句口号就能完成的,精神存在于物质之中,所以在强调大学精神的同时,我也想说说大学的物质或者说大学的肌体。物质匮乏时期依靠精神所创造的教育奇迹,西南联大就是最好的例子,但这种过分强调特例,忽视历史条件和现实境况的做法其实有些厚此薄彼。大学的肌体仍然是大学存在的根本,同时也是大学发展的基础。我们也要知道北大著名的不止有蔡元培,也有未名湖;武大著名的不仅有李四光,也有漂亮的樱花;厦大不仅有陈景润,更有号称中国最美的校园;南开至今保留着梁思成设计的学生宿舍,很多时候,精神也存在于大学的物质之中,大学的物质肌体体现了管理者办好教育的决心,是不是愿意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办公与学习环境。听过一句话叫食堂是学校的良心,大学精神的塑造是教师与学生的良心活,物质的建设则是管理者们的良心活。所以我认为大学的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包括教师、学生、管理者、社会各个主体之间无间的配合,既保存大学充沛的精神,也塑造大学健康的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