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4月,我校党委书记、校长陆丹策划组织了“大学”访谈专题,就如何更好地办好三亚学院,以人物采访和主题征文的形式问道于广大师生,掀起了全校师生关于理想大学理念、制度、文化、精神、品牌、教学、科研、育人、管理、创新等各个方面的大讨论,三亚学院师生在思考中寻答案,于讨论中求方法,这种思考讨论之风流行于校内之时,也吸引了众多校外专家学者的关注,近日,学校陆续收到了来自复旦大学、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多位专家、教授们关于“大学”话题的佳作,新闻网将陆续刊发,继续思考讨论之风,分享不同视角下的大学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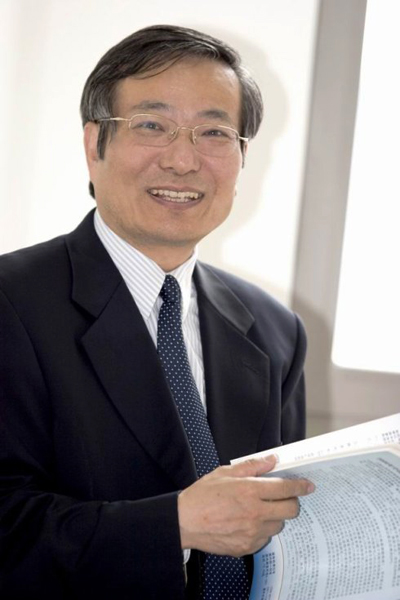
人物简介:周伟林: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三亚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城市发展研究》、《城乡规划》、《空间经济评论》、《上海国土资源》等刊物编委,《城市经济博士文库》和《现代城市经济学系列》主编。
美国加州大学克拉克·科尔教授研究发现,人类1500多年以前建立而至今仍然存在并以同样名字、同样方式、做着同样事情的组织,只剩下了85个,其中15个是宗教组织,另外70个是大学。
大学为什么能够百年昌盛,历久而弥新?我想大概因为它是创造和传播知识的殿堂,具有持续的价值观和理念,有着为此而奋斗献身的教师,常使学子们怀有理想和感恩之心,汇集众多聪慧之人一起发光发热,灿若星河,绵延不绝……
中国的大学产生较晚,近代以来尤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大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有各种类型的大学2000多所(含800多所普通本科院校、1200多所普通高职院校和近300所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等)。名牌大学一般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独特的文化和资源,但也有短时间内一跃成为成功大学的(如香港科技大学)。纵观大学的发展历程,其根本使命乃是创新和传播知识,而目标的推动、人才的集聚、开放的环境、品牌的塑造,则构成了大学建设的重要内涵。
学术和学问
如果仔细分辨大学与一般企业或机构的区别,其实不少企业或机构也专注于研发和发明专利,也可以是学习型组织,但大学则更以崇尚学问和传承知识为基石。19 世纪德国的洪堡,提出了“大学是由参与真理追求的师生组成的学者共同体”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逐步形成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大学发展模式。
大学鼓励学术自由创造以及学术训练,有利于提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相对而言,中国过去缺少定量分析的科学传统。比如关于中医有用无用的争论,可以说有了剑拔弩张的声势。硬说中医无用,显然是片面绝对了。但比较一下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境遇,我们还是得承认,当下中医确实没有超过老祖宗曾经达到过的水准,而西医却凭借实验科学的手段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且已形成了一个前景明朗的庞大的产业链。西医之所以可以产业化,是因为它可以按照标准流程来进行教学培训,可以为药品开发和器械设备投资,这些都可以产生规模效应。想想看,人类吸烟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只有当纸烟通过标准的流水线并借助品牌来生产和销售,才会诞生出一个烟草行业。同样,各国人民都要吃饭,然而并不是谁都能把吃饭产业化了。也只有当企业设计出符合现代生活节奏、按照标准化的流程运作的品牌,才能产生餐饮巨头。以麦当劳的汉堡包连锁店为例,管理被应用到原来是漫无规划的一般夫妻经营的小店中——它首先设计了最终产品,然后又重新设计了整个制作程序,包括设计操作工具,使得每一块肉、每一片洋葱、每一个面包、每一块炸土豆都一模一样,结果产生了一个时间精确、完全自动化的制作程序。接着,它着手研究顾客看重什么样的“价值”并将它定义为优质、可预知的产品、快捷的服务、绝对的干净以及亲切,最后根据这些设定标准,培训员工并配合这些规定给予报酬。中国虽然有很多特色菜系和名厨,我们的菜肴的色香味可以让世人垂涎欲滴,交口夸赞,但我们还没有见到有跨越全球的中餐品牌。
在现行应试教育体制下,我们的社会重学历轻能力,鄙薄技术工人,鄙薄职业教育培训,造成学生不愿意学技术,不甘心一辈子认认真真地干技术工人,这种教育体制与应试教育脱离实际需求很远,虽可以勉强为“中国制造”服务,却难以担当“中国创造”重任。彼得·德鲁克说,“企业家社会将挑战传统的教育和学习习惯及知识”,因为教育面对的是开放条件下多变的世界,刻舟求剑必将无功而返。
无疑,学术的精髓在于学问。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一个单词:“truth”(真理;也有人译为:让真理与你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复旦大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特别欣赏每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学和问。朱清时院士认为,不光是读书多、知识多、创新能力就强,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兴趣、好奇心、想象力和洞察力。牛顿17岁进入剑桥的三一学院,27岁成为数学教授,他的自白道出了一个纯粹学者的本性:“我觉得自己是个男孩,他在海边玩耍,不时地发现一块较为光滑的鹅卵石或较为漂亮的贝壳,开心不已,而真理的大海横亘在他的面前,未被探索过。”
创新与传播
《哈佛管理经典丛书》中有许多故事往往透出不同寻常的见解,其中“山雀与牛奶瓶”一则,就很耐人寻味。它说的是,在英国,由送奶工人把瓶装牛奶送到各家各户的门口,起初奶瓶都没有盖子,因此鸟很容易就能吃到瓶口的乳脂。山雀和红知更鸟,这两种普通的英国鸣禽都学会了从瓶口吸食乳脂。后来,人们用锡箔将奶瓶口封住,两种鸟对此有不同的应对。其中英国全部的山雀都学会了如何刺穿锡箔封口,这是由于它们觅食的时候总喜欢保持群体性,因而经历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制度化的学习过程”;相反,红知更鸟们却再也没能获得吸食乳脂的入口。尽管个别红知更鸟偶尔也会发现如何刺穿奶瓶封口,但这种本领不会被传给其它同类,因为红知更鸟是有领地观念的鸟类,雄知更鸟不允许其它雄性同类进入自己的领地,它们倾向于用敌对的方式交流,保持固定的领地而不相互穿越。这个故事说明了,群居的鸟类似乎学习得更快,进化得也更快,由此生存机会得到了提高。可见,具有如下特征的物种的解剖结构在物种进化过程中会加速,这些特征是:革新(有能力发明新的行为,创造出新的技巧以使自己用新方法利用环境);社会传播(个体的技巧可通过某种程序向整个群体传播);运动性(该物种的个体有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四处活动,它们群集一处而非相互隔绝)。
这个故事揭示的物种进化中的若干特征,与马歇尔在对地方化工业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所作的发现,在精神上非常接近。马歇尔观察到,“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所得到的利益非常大。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 这正如萧伯纳所言:如果两个人交换苹果,每个人手里还是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每个人的脑子就同时有两个思想。
大学里知识的创新与传播的机理也是如此。大学由各种专业院系组成,而每所学校的优势学科也不同。大凡是优势学科,都汇聚了优秀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他们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合作和交流机制。实际上,各个领域的领跑人并非是广泛而均匀地分布的,存在明显的集群形态。集群的存在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效率,而且改进了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尤为重要的是,集群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知识的传播,也更有利于新思想的形成。因为一个大学甚至一个学科的许多竞争优势,既由其内部决定,也可能来源于外部,即来源于其所在的城市和学科集群的交叉影响。这时,大学是通过影响传播和创新来产生竞争优势的。
与此相同,迈克尔·波特发现许多时候一国或一地的企业能在某些领域里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而且某项产业里的一批领先者都出现在同一个地区或国家。他探究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比如德国为何是全球印刷机产业、高级轿车、化工产业的集中地?瑞士为何是世界重要的药厂、巧克力食品与贸易业的基地?美国为何能在个人电脑、软件、信用卡、电影等产业中独占鳌头?意大利的企业为何可以在瓷砖、雪靴、包装机械以及工厂自动化设备方面表现强势?而日本企业又为何主导了家用电器、照相机、传真机以及工业机器人等产业?波特认为这都与集群的优势相关。
大学与城市
这世界上因大学而存在或形成了特殊创新文化氛围的城市乃至小镇有许多,比如英伦的剑桥和牛津。剑桥、牛津正好与伦敦构成奇妙的三角形。与剑桥的许多学院朝着剑河敞开不同,大多数牛津的学院被夹在broad street和high street之间,背对着大路。牛津的历史早于剑桥(剑桥从牛津分离而建)。两所学校难分伯仲,都有30多所学院。牛津长于文科,尤其是政治学和宗教学,只是现代社会更加重视科学研究成果,剑桥的排名遂多占了先。这些成立于中世纪的大学,都有大大小小的许多教堂和博物馆。掂量一所大学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其图书馆规模和体现宗教地位及财富的教堂的大小,以及饭厅,往往可以直观地做出判断。
同样,其他那些能够滋生创新的空间,往往也各显异彩。彼得·霍尔将城市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市民创新”的所在地,他区分过四种形式的创新:艺术型(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科技型(以生产流水线为特征的底特律、以高科技出名的帕拉阿托),文化-科技型(好莱坞与电影艺术)以及解决问题型(19世纪伦敦的污水处理)。
的确,凡是成功的大学和城市都是“学习”或“智能”的地方。人们尤其是企业家,围绕特定产业的适应能力以及预见新事物和发展机遇的能力,通过创新来保持竞争力,其中的真正的力量在于学会了如何学习。彼得·霍尔认为技术创新都发生在具有相似特征的那些地区,“那些地区的特点是没有丰富的固定资源,但是却具有一套发达的社会文化结构,支持理性的进步。这些地区可能是古老的、公认的、世界性的、自由的大都市,但是在很发达的地区和距离发达地区的边界之间经常会出现一些作为贸易中心(媒介中心)的城市区域。这些城市区域由于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而迅速地扩张,这些地区的移民率也很高,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认为这是极具实验性和大胆的事情。通常,他们有固定但不正式的交换技术知识和概念想法的组织。猎奇是他们的常态。无论在意见相同的个体还是意见相左的社会经济文化群体中,都会有高水平的协作,这就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原型。”
张五常在谈到经济学研究的集聚现象时,曾说道“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他的话里涉及了一种文化的集聚现象,那里充满激情岁月和成功人生的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从时间上来看,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学招收的刚从战场走来的退役军人,和中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进校的三届学生,确实是因为积累了太多的人生历练和动能而呈现出炫目的景象。人才成群涌现的景象似乎是一茬一茬的……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那么多人自己想上或者想让孩子上名牌学校,其实不光是图虚荣瞎折腾,深刻的内涵更在于编织有用的社会关系网。人的社会分层事实上存在一种“等高线”现象。在中国,尽管没有如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但是社会交往却是重视“圈子”的,讲究门当户对。这背后是寻求同质性,价值观相同,利益交流也相当,内部能够平衡和持续下去,甚至可以互为担保。但是阶层的门槛,也时常被底层的优秀分子以“学而优则仕”所打破。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进圈子很难,考大学是严进宽出,选拔干部同样如此,进了门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坐上了铁交椅。中国的名校毕业生都有一个体验,经常在各种重要场合碰到校友,并且一聊起来还发现有共同的朋友,于是免不了感叹一声“这世界真小”。其实并非这世界小,而是这圈子小。
品牌是生命
尽管《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强调,信息化把世界推平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平台,生产要素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流动。但世界扁平化以后,规则越来越起作用,决策中心更加有力,品牌集中度也大大提高。于是乎,pc视窗就是windows,飞机就是波音和空客,电影就是好莱坞,大学就是哈佛、剑桥,饮料就是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运动衣就是耐克、阿迪达斯;零售业方面,沃尔玛、家乐福在中国的快速扩张,使得很多本土零售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扁平化的世界,成了一个规则设计者大行其道的世界,一个世界名牌横扫天下的世界。只有品牌才成为消费者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因为当消费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判断时,往往依赖品牌进行信息鉴别。
诚然,学校教育活动的产出不同于社会的其他生产活动,的确难以衡量。一般常用的测试方法,偏重于测量认知技能,通常是考核或比较学习成绩而轻视其他,由于其他技能无法准确地进行度量,应试教育便大行其道。当然,mba教育摸索了一套事后的反馈办法,即根据毕业生受社会的欢迎程度和市场评价的结果——年收入来排名。
但无论如何,学校对人的影响只是全部人生知识和经验的一部分,而且其中的成效还难以度量。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要那样用力地去挑选学校呢?其实,人们挑选学校所参考的指标虽然形式上有分数等限制,但学校和知名教师的影响力以及专业的排名仍然是其权衡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决定教育质量(学习成绩)的生产函数,包括了家庭环境、同龄人特征以及教师的影响等。家境好又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为子女提供了更优越的家庭环境,鼓励其看书,与其交流思想,参与设计职业规划,家长的建议和经验会对子女有帮助。所谓同龄人效应,表现为如果一个学生周围都是聪明好学的伙伴,那么他就会学到更多。聪明的学生具有外部性,好学的同龄人能相互促进,因为有了合作和竞争的学习氛围,就连成绩差的同学也能从中受益。而教学经验丰富、有责任心、能因材施教的教师,能够帮助学生学得更多而且更加有效。因此,学生选择不同的学校,权衡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学费或者生活成本的不同组合,都是为了获得较好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的外部效应。
学校教育教育为何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功能?学校的产出是什么?它对人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无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开掘人的德智体美的技能。其中智育是读写、数学以及逻辑的基本认知技能的训练,这些技能是就业和生活的必要条件;而德育培养人的社会技能,以便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教人学习如何互相交流与合作;体育和美育则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富于情趣,身心健康。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一座大学的不朽精神?剑桥有800多年历史,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生生不息。中国大学虽有进步(标志是:入学率大规模提高,硬件投入增加,国际交流增多),并且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但仍然是形似而非神似。我跑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包括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一桥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和孟买大学以及港台的几所大学等,比较下来,觉得中国大陆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较高,硕士生教育部分较好,博士生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要逊色不少。而本科生教育质量,尤其是top10所大学教育质量较高,主要由考生质量保证(想想看,那是每年近千万考生作为基数筛选出来的精英!)。中国大学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恐怕少不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前提还需要路子对头。



